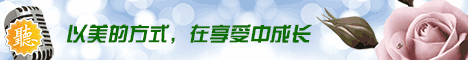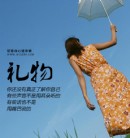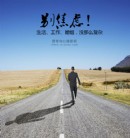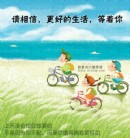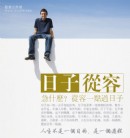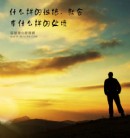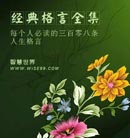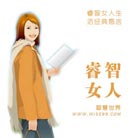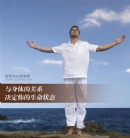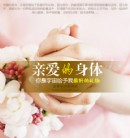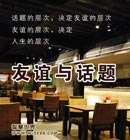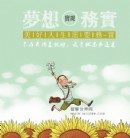宋明理学讲求“慎独”,它最先见于《礼记·中庸》:“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,可离非道也。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“慎独”作为修身的方法,强调的是在没有任何外在监督的情况下仍然能坚守内心的道德信念。这其实是要求由外在的“他律”转化为完全内在的“自律”,“慎独”是把道德规范内在化,使其成为指导自我行为的准绳,这本是修身养性的一件好事。
然而任何事情都是过犹不及,过分的道德压力往往容易使人失去幸福的感觉,因此还不如直接面对过失,坦然承认过失来得痛快。
就如金圣叹所言:“身非圣人,安能无过。夜来不觉私作一事,早起怦怦,实不自安。忽然想到佛家有布萨之法,不自覆藏,便成忏悔,因明对生熟众客,快然自陈其失。不亦快哉!”
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当过失发生了,与其遮遮掩掩、私下悔恨,不如坦然承认,所谓“布萨”即是僧众自我检查有无违犯戒律之事,如果违犯,则按照情节轻重进行忏悔,“对生熟众客,快然自陈其失”本身就是一件洒脱磊落的事情,心中的石头顿时落地,浑身畅快,快乐也就如期而至了。
其实每个人的内心或多或少都有“阴暗”的一面,比如幸灾乐祸的心理,试看第一则:“朝眠初觉,似闻家人叹息之声,言某人夜来已死。急呼而讯之,正是一城中第一绝有心计人,不亦快哉!”
再看第三十则:“看人风筝断,不亦快哉!”听闻心机尤深的权谋者撒手人寰,没有假装悲戚;看到别人的风筝线断飘飞,不禁哑然失笑。这些都活脱脱地展现了明代江南文人厌弃礼法、自见本心的真诚与洒脱,获得这种心灵的自适才是真正的幸福。
身心的自适与快意当然需要一颗敏感的心灵去体悟。幸福与否全在于个人的感觉,感觉敏锐的人,会在不经意处获得幸福的体验;而感觉迟钝的人,则常常与幸福擦肩而过,甚至怨天尤人,时时、事事、处处引为不幸,这样日子当然不好过。
然而金圣叹绝不是这样的忧郁者,在他洒脱的精神中其实包含着一颗敏感的心灵,能于人伦日用生活琐碎中见出幸福的瞬间:“十年别友,抵暮忽至。开门一揖毕,不及问其船来陆来,并不及命其坐床坐榻,便自疾趋入内,卑辞叩内子:‘君岂有斗酒如东坡妇乎?’内子欣然拔金簪相付。计之可作三日供也。不亦快哉!”有朋自远方来本就是一件快乐的事情,朋友之间也没有虚假的客套,主人直接趋入内室,请夫人置办酒水与友人相酌,妻子解意会情,拔金簪典当相助,友情的真挚、爱情的浓郁跃然纸上。作者感到的也都是幸福的瞬间,并没有因为经济上的困顿而悲悲戚戚,失去幸福的体验。
只要用心体悟,幸福感是触处可拾的:“重阴匝月,如醉如病,朝眠不起。忽闻众鸟毕作弄晴之声,急引手搴帷,推窗视之,日光晶荧,林木如洗。不亦快哉!”
“推纸窗放蜂出去,不亦快哉!”
“读《虬髯客传》,不亦快哉!”
……
天气由阴转晴,心情也随之转晴,是快乐的;推窗放生,功德虽小,快乐却多;读书怡情,亦可收获快乐。总之,只要有一颗认真体悟的心灵,生活中的快乐就不胜枚举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